
浙江宣传:读书就是交友


独家抢先看
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中国人相信打开人生需要行走与阅读,西方也有一句谚语“You are what you read(你的阅读造就了你)”,阐明阅读对人格的深刻塑造。最近,国务院批复设立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,鲜明昭示读书不仅关乎个人,也关乎文明传承发展。
明代于谦有句诗,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。书与人,有缘才相见,更难得性情相投、心神相契。因此说,读书就是交友。

图源:“杭州发布”微信公众号
一
阅读是读者与作者、与书中人的相遇,在你来我往间,激荡出种种体验。评论家卡莱尔说:“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,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。”读书就是“登门造访”这些珍贵的灵魂。
读经书,向贤者问道。孔子读《诗》至《小雅》,不禁喟然长叹;苏东坡读《庄子》,感慨“吾昔有见,口未能言,今见是书,得吾心矣”。先贤尚如此,今人捧卷,又怎能不心有戚戚、顿生共鸣?《中庸》谈如何致中和,《论语》琢磨怎样立德修身,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深究万物至理,读之思之,让我们得以观照自我,从而出入世间。
读史书,听长者开讲。我们于《史记》中,看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拂去历史的烟云,显现人性的光辉与幽微;又在《资治通鉴》里,随司马光溯流而上,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。经由希罗多德《历史》、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、斯塔夫里阿诺斯《全球通史》等,我们放眼古今中外,纵览人类文明脉络。
读小说,似远客来访,一起围炉夜话。历经八十一难的唐僧取经团队,无尽“孤独”的布恩迪亚上校,“美丑共生”的敲钟人卡西莫多……在作家的讲述中,这些人物从四面八方而来,携一路风霜与我们相会。许多作家也对作品和读者怀揣期许,托尔斯泰说“作家要唤起一种经验过的情感,这种情感要以别人可能体验到的方式交流”,而《人世间》作者梁晓声也思考:“我自己写的书是不是也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好朋友呢?”
读诗歌,若少年同游,一时风云际会。登高望远,“会当凌绝顶”的壮志在胸;快意江湖,化身“银鞍白马度春风”的五陵少年;愁肠百转,一句“剪不断理还乱”脱口而出。据说,明代袁宏道偶然见到徐文长的诗稿,“读复叫、叫复读”。郭沫若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短诗《歌》,凭“上有冰天风入冻,下有积雪之河川”写出东方意蕴,堪称“再创作”。读诗,读的就是刹那之间的“闪电”。
作者用文字笔墨建造一个个世界,读者用心品读就能推门入园畅游其中。杨绛因此说,“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,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,不问他什么专业,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,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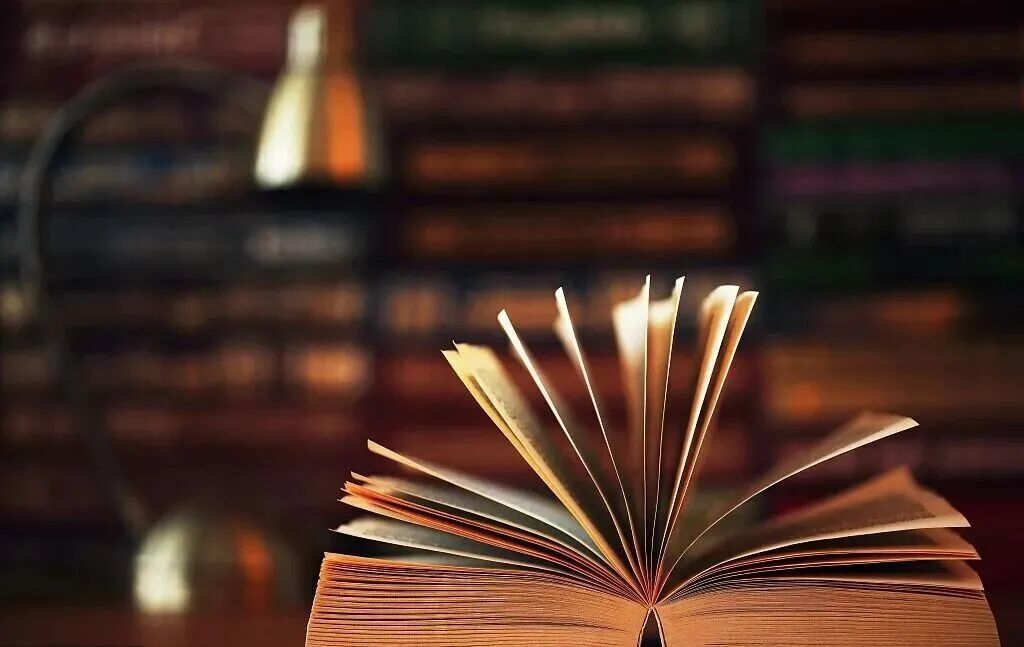
图源:“央视网”微信公众号
二
如今,书籍浩如烟海,新作层出不穷。优先读哪些书,需要甄选,不妨以交友之道比照,孔子说“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”,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读书提供了清晰标准。
读正直的经典。清代袁枚曾以建筑作喻,“四子书如户牖,九经如厅堂,十七史如正寝”。任凭时光流转,经典的殿堂始终岿然矗立。唯有在元典、经典的浸润中,方能奠定“三观”根基,涵养价值判断与审美品位。
柳宗元读书,以《书》求其质,以《诗》养其恒,以《礼》习其宜,坦言“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”。梁启超也主张,诸经、诸子、《四史》、《通鉴》等书当入精读之列,须“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,读时一字不放过,读完一部才读别部”。真正值得倾心拜读、反复重读的,正是那些引你沉思其中、助你登堂入室的经典。
读诚意满满的作品。以功利之心交友,情谊终难长久,读书同样如此。那些倾注匠心深情的作品,即便不是鸿篇巨制,也能动人心弦,比如史铁生《秋天的怀念》、季羡林《我的母亲》,写出温柔而伟大的母爱;蒋坦的《秋灯琐忆》、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,只言片语中蕴含夫妻深情。
阅读这类作品,我们会共情他人的命运,为其际遇悲欢唏嘘;合上书页,那些挣扎、坚韧与希望并未消逝。每多一位这样的“挚友”,我们的生命就多一分丰盈。
读有意思的文字。看见妙趣横生的文字,如同与一位“灵魂有趣”的朋友对谈交流,自然惬意开怀。阅读时不必有负担,可一气读完,也可随兴搁置,更可跳览涉猎,自在徜徉,用林语堂的话说,“最适宜的阅读方式就是须出于写意”。
古今中外,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据说,达尔文爱读爱情小说,罗斯福偏好侦探小说。当下很多人爱读丰子恺、汪曾祺的文字,时常感到草木含情、人间有趣。比如丰子恺的散文《吃酒》,讲到西湖畔的一个酒徒,于湖边钓得虾来,到店里买酒一斤,自己用开水现场烫虾吃酒,其滋味跃然纸上。
构建自己的“精神朋友圈”,有良师益友指导引路,又得挚友慰藉心灵,亦有趣友谈天论地,自然能享读书之乐、成进益之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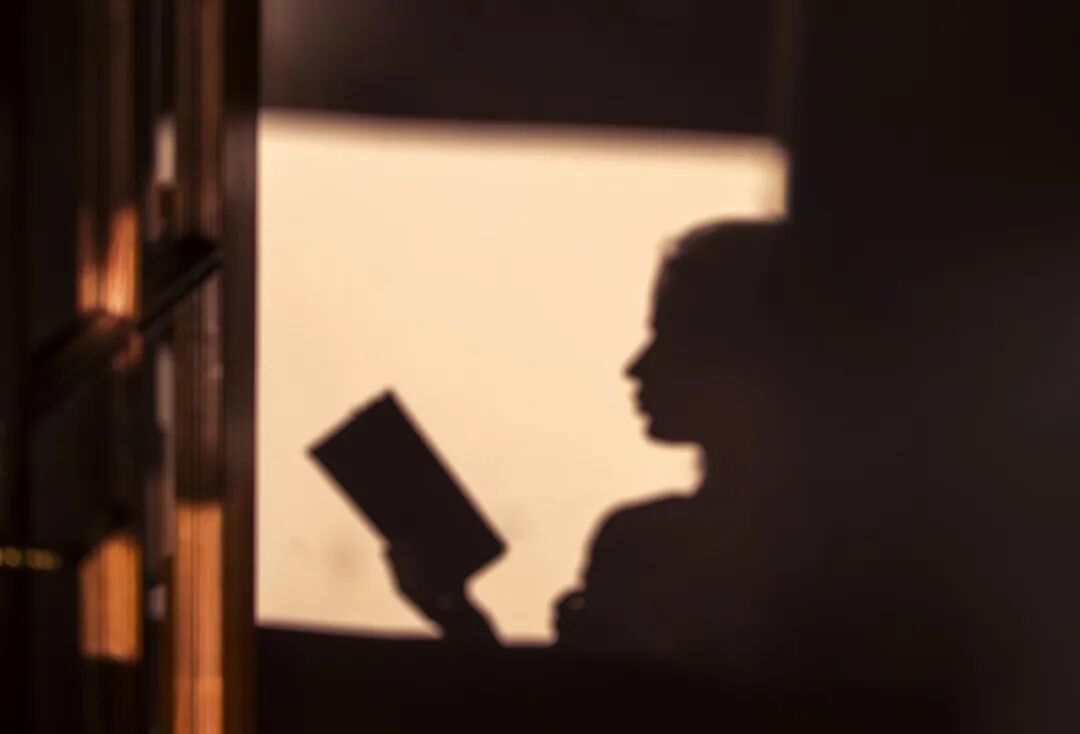
图源:视觉中国
三
世上有无数的人,也有无数的书。欣赏一个人,始于颜值,敬于才华,合于性格,忠于人品,读书亦当如此。
值得深交的“人生之书”,理应反复读、一起走。与好书建立交情急不得,也强求不来,它们初时只是架上近邻,经久才成知交。苏轼贬谪黄州,仍坚持每天抄写《汉书》。国学大师黄侃则把《昭明文选》批注十遍,“旧书不厌百回读”,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悟。
人生之书能让人常读常新、汲取养分,反复品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其精妙之处。毛泽东好读书、善读书,他对《共产党宣言》阅读不下一百遍,曾讲道:“有时只阅读一两段,有时全篇都读,每读一次,我都有新的启发。”撰写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时,他还翻阅多次。
偶然相逢的“点头之交”,可以大略看,也可以多观察。陶渊明“泛览周王传,流观山海图”,怡然自得地说“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何如”。很多时候,我们阅读只为浏览资讯或消遣娱乐,那样浮光掠影又何妨?某个阳光正好的午后,信手翻开一本杂志,给忙碌生活留片刻闲暇。
泛读也是一种重要的准备,这样当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时,才能知道从何入手。因此,余光中说,真正会读书的人,一定深谙略读之道,即使面对千百本好书,也知道远近缓急之分。若觉《史记》艰涩,就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进;若惧《红楼梦》浩繁,大可先随刘姥姥共入大观园。没有平日的“点头之交”,哪有日后的“深情款款”?
曾经意气相投却失散在人海的“季节性朋友”,可以从此怀念,也可以再续前缘。周国平曾这样描摹人与书关系的微妙,“有邂逅,离散,重逢,诀别,眷恋,反目,共鸣,误解”,阶段不同,心境各异。所以才会少年时读金庸,向往快意恩仇;青年时读金庸,慢慢理解“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”;待到中年后重读,或许为追忆年少轻狂。
有些大部头,一时读不进去也无须焦虑,毕竟连名家都有反复尝试才能读透的时候。冰心十二三岁初读《红楼梦》,只觉“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”,中年后再度展卷,才读懂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的深意。
总之,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愿我们始终与书为友,以阅读点亮人生。
来源:浙江宣传





